【摘要】
【裁判要旨】職工在工作時(shí)間和工作場(chǎng)所內(nèi)突發(fā)疾病,因未得到及時(shí)搶救致使職工成為植物人的情形,不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規(guī)定中的事故范圍,因而不能認(rèn)定為工傷。事故的內(nèi)涵和外延應(yīng)當(dāng)解釋為外力所致的意外性傷害,而不能包羅萬(wàn)象;《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五條的法條定位是將原本不屬于工傷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的情形視同為工傷,在立法技術(shù)上采用了明確列舉的方式對(duì)第十四條進(jìn)行補(bǔ)充,因而第十四條各項(xiàng)內(nèi)容也不存在進(jìn)一步解釋的空間,否則第十五條的規(guī)定就失去了補(bǔ)充條款的實(shí)際意義,違背立法的目的。
案號(hào): 一審:(2012)崇行初字第41號(hào) 二審:(2013)錫行終字第0015號(hào)
【案情】
原告:王光輝。
被告:無(wú)錫市人力資源和社會(huì)保障局。
第三人:無(wú)錫市第四人民醫(yī)院。
江蘇省無(wú)錫市崇安區(qū)人民法院查明,王光輝系無(wú)錫市第四人民醫(yī)院腫瘤外科醫(yī)生、副主任醫(yī)師。其主要工作內(nèi)容為:在科主任的統(tǒng)籌安排下做好病人的管理工作,包括門(mén)診、手術(shù)、查房、會(huì)診、討論以及指導(dǎo)下級(jí)醫(yī)師開(kāi)展具體工作。2011年1月至6月6日,無(wú)錫市第四人民醫(yī)院共安排王光輝值夜班18班次,平均每月2至4班次不等。王光輝作為副主任醫(yī)師所值夜班均為二線班,不需值班坐班或巡視,可以在休息室休息,只有一線值班醫(yī)師出現(xiàn)無(wú)法處理的情況才請(qǐng)二線值班醫(yī)師就診。2011年6月6日晚王光輝值夜班,當(dāng)晚未發(fā)生需要二線值班醫(yī)師就診情況,王光輝一直在休息室休息。2011年6月7日上午8時(shí)20分許,因王光輝上午未出專(zhuān)家門(mén)診,同事在值班室發(fā)現(xiàn)其不適,便送去治療。無(wú)錫市第四人民醫(yī)院出具的醫(yī)療證明書(shū)中載明王光輝臨床印象為后腦循環(huán)梗死、植物狀態(tài),后王光輝轉(zhuǎn)至南京紫金醫(yī)院治療,至今仍處于植物人狀態(tài)。2011年12月23日,王光輝的妹妹為其向無(wú)錫市人力資源與社會(huì)保障局提出工傷認(rèn)定申請(qǐng),并提交了相關(guān)申請(qǐng)材料。無(wú)錫市人力資源與社會(huì)保障局受理審核后作出工傷認(rèn)定決定書(shū),認(rèn)為王光輝的情形不符合《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guī)定的情形,不予認(rèn)定為工傷和視同工傷,并分別向王光輝和無(wú)錫四院送達(dá)該決定書(shū)。
原告訴稱(chēng):2011年6月6日端午節(jié),王光輝在醫(yī)院值大夜班期間突發(fā)腦梗塞,直至第二天早上8時(shí)20分換班時(shí)才被發(fā)現(xiàn),造成搶救延誤,被無(wú)錫市第四人民醫(yī)院診斷為后腦循環(huán)大面積梗死,目前處于植物人狀態(tài),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原告向被告無(wú)錫市人力資源與社會(huì)保障局提出工傷認(rèn)定申請(qǐng),被告受理后,不做任何事實(shí)調(diào)查,便作出不予認(rèn)定工傷和視同工傷的決定。原告認(rèn)為:1.被告認(rèn)定事實(shí)不清。原告長(zhǎng)期患有高血壓,單位安排其長(zhǎng)期上大夜班,工作強(qiáng)度大,導(dǎo)致原告發(fā)病,且單位值班室條件簡(jiǎn)陋、無(wú)巡查制度,王光輝發(fā)病后沒(méi)有及時(shí)被發(fā)現(xiàn),搶救延誤,錯(cuò)過(guò)最佳搶救時(shí)間,造成原告目前呈植物人狀態(tài),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在性質(zhì)上屬于單位事故。2.被告適用法律錯(cuò)誤。原告的情形屬于在工作時(shí)間和工作場(chǎng)所內(nèi),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應(yīng)當(dāng)適用《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之規(guī)定認(rèn)定為工傷。即使原告的情形不適用第十四條之規(guī)定,被告在適用法律時(shí)也過(guò)于機(jī)械,正確的處理方式應(yīng)該是對(duì)《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五條采用目的性解釋以及擴(kuò)大解釋?zhuān)J(rèn)定原告視同工傷。
被告無(wú)錫市人力資源與社會(huì)保障局辯稱(chēng):王光輝在工作時(shí)間突發(fā)疾病,不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工傷認(rèn)定和視同工傷的范圍,被告作出的工傷認(rèn)定決定程序合法,認(rèn)定事實(shí)清楚,結(jié)論符合法律的規(guī)定,請(qǐng)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qǐng)求。
第三人無(wú)錫市第四人民醫(yī)院稱(chēng)尊重法院的判決。
【審判】
江蘇省無(wú)錫市崇安區(qū)人民法院經(jīng)審理認(rèn)為:《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分別以列舉的方式規(guī)定了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工傷和視同工傷的情形,其中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規(guī)定,職工在工作時(shí)間和工作場(chǎng)所內(nèi),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工傷。《工傷保險(xiǎn)條例》中的事故傷害,一般是指職工在工作過(guò)程 中發(fā)生的因外力導(dǎo)致的人身傷害或者急性中毒等事故。王光輝長(zhǎng)期患有高血壓病,其事發(fā)當(dāng)天在值班期間發(fā)病的情況,顯然不屬于受到事故傷害的范疇。《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xiàng)規(guī)定,職工在工作時(shí)間和工作崗位,突發(fā)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shí)之內(nèi)經(jīng)搶救無(wú)效死亡的,視同工傷。從《工傷保險(xiǎn)條例》的立法目的來(lái)看,工傷保險(xiǎn)是對(duì)勞動(dòng)者在工作或其他職業(yè)活動(dòng)中因意外事故或職業(yè)病造成的傷害給予補(bǔ)償?shù)纳鐣?huì)保障制度,認(rèn)定工傷的前提是“因工”,因此,一般來(lái)講,疾病應(yīng)不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保護(hù)的范圍。但《工傷保險(xiǎn)條例》中上述條款的規(guī)定體現(xiàn)了立法對(duì)勞動(dòng)者傾斜保護(hù)的原則和目的,讓突發(fā)疾病納入工傷保護(hù)的范疇。同時(shí),為避免將突發(fā)疾病無(wú)限制地?cái)U(kuò)大到工傷保險(xiǎn)的范圍,又作出了限制性規(guī)定,即明確了適用該規(guī)定視同工傷必須同時(shí)符合三個(gè)要件:工作時(shí)間、工作崗位、突發(fā)疾病死亡或者48小時(shí)之內(nèi)搶救無(wú)效死亡。這是強(qiáng)制性的法律規(guī)定,應(yīng)嚴(yán)格執(zhí)行。故王光輝在醫(yī)院值班期間突發(fā)疾病經(jīng)搶救至今仍處于植物人狀態(tài)不符合《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xiàng)的規(guī)定,也不符合《工傷保險(xiǎn)條例》規(guī)定的其他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因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執(zhí)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第56條第(4)項(xiàng)之規(guī)定,判決駁回王光輝的訴訟請(qǐng)求。
原告王光輝不服一審判決,向無(wú)錫市中級(jí)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上訴人王光輝稱(chēng):王光輝是在工作時(shí)間、工作場(chǎng)所因工作原因突發(fā)疾病后延誤搶救導(dǎo)致喪失最佳醫(yī)治時(shí)間而變成植物人,延誤搶救就是重大事故,因而本案應(yīng)適用《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關(guān)于工傷認(rèn)定的規(guī)定。另外,上訴人從高血壓病發(fā)展到腦梗塞,是一個(gè)緩慢過(guò)程,上訴人從發(fā)病到致殘,最終成為植物人,與常年的工作疲勞、單位設(shè)施設(shè)備不完善、勞動(dòng)條件和勞動(dòng)環(huán)境不良、管理不善等有著極其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原審第三人安排其長(zhǎng)期不規(guī)律的工作和高強(qiáng)度的勞動(dòng),是加速上訴人疾病積累和突發(fā)的重要因素。綜上,請(qǐng)求撤銷(xiāo)原審判決,并改判確認(rèn)王光輝在工作時(shí)間、工作地點(diǎn)發(fā)生的事故屬于工傷。
江蘇省無(wú)錫市中級(jí)人民法院經(jīng)審理認(rèn)為:《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規(guī)定,既明確了認(rèn)定工傷和視同工傷的范圍,同時(shí)也相對(duì)確定了不應(yīng)認(rèn)定工傷或視同工傷的界線,突發(fā)疾病經(jīng)搶救后的傷亡情形不應(yīng)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所指的事故范圍,而搶救是否有延誤并不影響《工傷保險(xiǎn)條例》對(duì)事故的判斷。因此,本案中上訴人的情形不符合《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認(rèn)定工傷的規(guī)定,故上訴人王光輝提出延誤搶救屬于工傷認(rèn)定的事故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上訴人的情形同樣也不符合第十五條第(一)項(xiàng)視同工傷的規(guī)定。上訴人提出的其發(fā)病與常年工作疲勞、單位設(shè)施設(shè)備不完善、勞動(dòng)條件和勞動(dòng)環(huán)境不良、管理不善等有著極其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等事由,并不屬于本案中工傷認(rèn)定的事由,其應(yīng)通過(guò)其他救濟(jì)途徑主張權(quán)利。綜上所述,一審判決程序合法,認(rèn)定事實(shí)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yīng)予維持。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應(yīng)予駁回。據(jù)此,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xiàng)的規(guī)定,依法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píng)析】
綜合全案,可以歸納認(rèn)為,本案爭(zhēng)議的焦點(diǎn)是上訴人王光輝在值班期間、工作崗位突發(fā)疾病因未得到及時(shí)搶救是否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規(guī)定的工傷認(rèn)定中的事故。經(jīng)過(guò)系統(tǒng)的考察和研究,筆者認(rèn)為職工在工作期間和工作崗位突發(fā)疾病未得到及時(shí)搶救的情形不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中關(guān)于事故的規(guī)定。
一、事故的語(yǔ)詞涵攝及其性質(zhì)考察
在現(xiàn)代漢語(yǔ)言學(xué)中,“事故”通常是指“在生產(chǎn)作業(yè)中意外的損失或?yàn)?zāi)禍”。{1}純粹從語(yǔ)言學(xué)的角度分析,事故的蘊(yùn)涵應(yīng)該包括兩個(gè)方面:一是發(fā)生的環(huán)境與生產(chǎn)、作業(yè)的環(huán)境相關(guān),二是具備意外性,如交通事故、火災(zāi)事故、爆炸事故等。如果事故發(fā)生的環(huán)境與生產(chǎn)、作業(yè)毫無(wú)關(guān)聯(lián)且不具備意外、突發(fā)性的特點(diǎn),就不能稱(chēng)之為事故,至少不能稱(chēng)之為《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中的事故,而只能認(rèn)定為事情或者事件。事情或者事件的語(yǔ)詞涵攝,在語(yǔ)言學(xué)上是一種純粹客觀的描述性詞條,本身不包含任何色彩;事故則不同,事故在語(yǔ)言學(xué)上蘊(yùn)涵了特定色彩、特定的指涉,即與生產(chǎn)、作業(yè)環(huán)境相關(guān)的突發(fā)性的事件。事故較之于事情或者事件的色彩化限定,對(duì)于后續(xù)的責(zé)任承擔(dān)也具有解釋學(xué)上的意義。
在法律法規(guī)中,目前尚未有專(zhuān)門(mén)性法律條文對(duì)于事故進(jìn)行嚴(yán)格界定。1986年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局頒布了《企業(yè)職工傷亡事故分類(lèi)標(biāo)準(zhǔn)》,其中對(duì)于傷亡事故做出了具體的解釋和認(rèn)定,主要是指:企業(yè)職工在生產(chǎn)勞動(dòng)過(guò)程中,發(fā)生的人身傷害、急性中毒等意外事件。《企業(yè)職工傷亡事故分類(lèi)標(biāo)準(zhǔn)》所列的事故類(lèi)別共有19項(xiàng),如物體打擊、車(chē)輛傷害、機(jī)械傷害、火災(zāi)、坍塌、爆炸等事故類(lèi)別。分析此19項(xiàng)具體的事故類(lèi)別可以看出,其共同的特征是由于外力的原因所導(dǎo)致。綜合現(xiàn)代漢語(yǔ)語(yǔ)言的特點(diǎn)和國(guó)家相關(guān)部門(mén)作出的規(guī)定,我們可以認(rèn)為:事故在發(fā)生的原因上表現(xiàn)為外力侵害而非其他傷害,在性質(zhì)上可歸咎于生產(chǎn)作業(yè)中因管理、監(jiān)督不善所導(dǎo)致的、能夠追究相關(guān)部門(mén)或者人員責(zé)任的意外傷害。
在本案中,上訴人王光輝在工作時(shí)間和工作場(chǎng)所內(nèi)突發(fā)疾病未及時(shí)搶救致使其成為植物人的情形,在發(fā)生的原因上主要是上訴人本身身體素質(zhì)這一內(nèi)在的原因,因客觀條件導(dǎo)致未能及時(shí)搶救的外在因素只是或然性的因素,無(wú)論如何在性質(zhì)上也不能認(rèn)為未及時(shí)搶救屬于外力傷害,故不能認(rèn)定為《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關(guān)于工傷事故認(rèn)定中的事故。
就實(shí)踐而言,對(duì)于因未得到及時(shí)搶救而致使職工成為植物人的情形是否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工傷認(rèn)定中的事故,還可以從未得到及時(shí)搶救的原因方面進(jìn)行深入分析。一般來(lái)講,未得到及時(shí)搶救在原因歸責(zé)的角度可以從以下兩個(gè)方面分析:一是負(fù)有救助義務(wù)的其他職工個(gè)人故意、惡意行為所致。例如,職工被發(fā)現(xiàn)發(fā)生意外后,相關(guān)責(zé)任人員或者其他負(fù)有救助義務(wù)的人員故意不積極救助或者故意阻礙他人救助導(dǎo)致失去最佳救助機(jī)會(huì)。在這種情形中,其他職工的個(gè)人行為由于缺乏事故認(rèn)定中的突發(fā)性、意外性要素,顯然不能認(rèn)定為事故,而只能認(rèn)定為具有借助客觀因素非法侵害他人生命、健康、以不作為的方式實(shí)施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行為,一旦查明事實(shí)真相,相關(guān)責(zé)任人員可能因此會(huì)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二是囿于單位管理疏漏、職工本人身體素質(zhì)以及生活習(xí)慣等原因客觀上所造成的無(wú)意性未及時(shí)搶救。應(yīng)該說(shuō),單位職工發(fā)生意外且發(fā)生未及時(shí)搶救的后果,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單位工作安排管理制度存在管理上的疏漏與其他諸如職工生活習(xí)慣、身體素質(zhì)等因素均有可能導(dǎo)致職工身處險(xiǎn)境而未及時(shí)搶救。然而,不管是單位管理制度上的疏漏還是其他原因,只要是沒(méi)有故意或者惡意不搶救行為的主導(dǎo),就難以認(rèn)定未及時(shí)搶救的后果是工傷認(rèn)定中的事故。事實(shí)上,職工在單位值班突發(fā)疾病未得到及時(shí)搶救的情形,在性質(zhì)上是否可以歸責(zé)于單位,需要仔細(xì)分析:職工在值班中,單位是否具有守護(hù)值班職工生命健康的義務(wù)?如果職工受到外力的傷害,比如遭遇地震、火災(zāi)等自然原因引起的傷害以及搶劫、搶奪等人為原因造成的傷害,自然可以認(rèn)定為事故,這些不可預(yù)測(cè)的后果在責(zé)任承擔(dān)上具有法理上的正當(dāng)性。但是,因?yàn)槁毠ぷ陨硗话l(fā)疾病導(dǎo)致出現(xiàn)類(lèi)似于本案中的情形,單位當(dāng)然沒(méi)有義務(wù)為值班職工的生命健康再派人為其“值班”,這在實(shí)踐中不現(xiàn)實(shí),也不存在理論上的依據(jù)。申言之,即使單位的管理存在漏洞,但是這種漏洞在性質(zhì)上不夾雜任何價(jià)值判斷因素的無(wú)意狀態(tài),即管理漏洞的存在不能認(rèn)為單位存在過(guò)錯(cuò)。當(dāng)然,囿于管理漏洞所產(chǎn)生的后果,職工與單位可以通過(guò)雇主責(zé)任或者其他民事訴訟的渠道解決相應(yīng)的賠償糾紛,而不能想當(dāng)然地將其認(rèn)定為工傷事故。
二、《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與第十五條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分析
本案中,上訴人王光輝及其委托代理人均認(rèn)為,對(du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在工作時(shí)間和工作場(chǎng)所內(nèi),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工傷”的規(guī)定不局限于常規(guī)的理解,應(yīng)該從有利于利益遭受損傷的職工的權(quán)益最大化保護(hù)、從第十五條視同工傷擴(kuò)大解釋的雙重角度去重新定位第十四條中事故的內(nèi)涵和外延,即未得到及時(shí)搶救本身就應(yīng)該認(rèn)定為事故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由此可知,對(du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中的事故涵攝的理解,上訴人一方存在不同的認(rèn)識(shí)。
事實(shí)上,本文評(píng)析第一部分中關(guān)于事故的語(yǔ)義涵攝、性質(zhì)考察的學(xué)術(shù)界定,意義也僅僅局限于對(duì)《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規(guī)定的文義解釋。然而,對(duì)于法律條文的文義解釋?zhuān)鐣?huì)各方主體均具有解釋的權(quán)利,不同的解釋結(jié)論之間可能存在矛盾,而且矛盾的各方各執(zhí)一詞,并不能得出較為一致的認(rèn)識(shí),這是文義解釋的弊端。比如,本案中的爭(zhēng)議焦點(diǎn)“未得到及時(shí)搶救”是否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規(guī)定的事故,利益受損方(當(dāng)事人)與利益費(fèi)受損方(裁判者與評(píng)論者)基于立場(chǎng)的不同,分別得出不同的解釋結(jié)論。
因而,在司法實(shí)踐中,司法裁判者在面對(duì)不同解釋主體基于不同的解釋立場(chǎng)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不能得出趨向一致的解釋結(jié)論時(shí),就需要采用其他不會(huì)因解釋立場(chǎng)的差異而導(dǎo)致解釋結(jié)論不同的解釋方法——體系解釋。所謂體系解釋?zhuān)侵父鶕?jù)法律條文在整部法律中的地位,聯(lián)系相關(guān)法條的含義,闡明其規(guī)范意旨的解釋方法。{2}這是因?yàn)椋胺蓷l文只有當(dāng)它處于與它相關(guān)的所有條文的整體之中才顯出其整體的含義,或它所出現(xiàn)的項(xiàng)目會(huì)明確該條文的真正含義。有時(shí),把它與其他條文——同一法令或同一法典的其他條款——比較,其含義也就明確了。”{3}遵循體系解釋的基本原理,在本案的法律適用過(guò)程中,筆者對(du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的規(guī)定進(jìn)行了較為深刻的思考。
筆者認(rèn)為,職工在值班過(guò)程中突發(fā)疾病未得到及時(shí)搶救是否屬于《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規(guī)定的工傷事故,在邏輯上還需要結(jié)合《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五條的規(guī)定進(jìn)行體系上的解釋和研究。《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分別以列舉的方式規(guī)定了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工傷和視同工傷的情形,其中第十四條第(一)項(xiàng)規(guī)定,職工在工作時(shí)間和工作場(chǎng)所內(nèi),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工傷。第十五條第(一)項(xiàng)規(guī)定,職工在工作時(shí)間和工作崗位,突發(fā)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shí)之內(nèi)經(jīng)搶救無(wú)效死亡的,視同工傷。所謂視同工傷,在學(xué)理上主要是指:這類(lèi)情形本不應(yīng)屬于工傷保險(xiǎn)的認(rèn)定范疇,但考慮到其可能與工作存在著一定聯(lián)系,為了體現(xiàn)工傷保險(xiǎn)認(rèn)定的人性化和道義性,《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五條以列舉的立法方式明確將符合一定條件的情形視同工傷對(duì)待。這在邏輯上可以認(rèn)為:《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四條與第十五條之間關(guān)于工傷認(rèn)定是一種主文與輔文的補(bǔ)正關(guān)系。具體而言,在認(rèn)定工傷保險(xiǎn)是否成立時(shí),首先應(yīng)當(dāng)從第十四條的規(guī)定入手,如果職工遭遇傷害的情形不能適用第十四條的規(guī)定,那么可以再比對(duì)第十五條的規(guī)定。在這種補(bǔ)正關(guān)系的立法技術(shù)中,我們應(yīng)當(dāng)明確的是:《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五條的法條定位是將視同工傷的情形采用明確列舉的方式對(duì)第十四條進(jìn)行補(bǔ)充,因而在工傷保險(xiǎn)認(rèn)定中,在比對(duì)第十五條(輔文)之后依然未能找到可以認(rèn)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法律依據(jù)時(shí),在法律適用的邏輯學(xué)角度也就宣告了“不能認(rèn)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這一結(jié)論的成立,同時(shí)也就意味著第十四條(主文)各項(xiàng)內(nèi)容也就不存在進(jìn)一步解釋的空間,否則第十五條的規(guī)定就失去了補(bǔ)充條款的實(shí)際意義,也就會(huì)違背立法的真正意旨。質(zhì)言之,如果我們?cè)诒葘?duì)輔文時(shí)不能得出有利的結(jié)論就隨便地回到主文,再次要求進(jìn)一步拓展主文的解釋空間,那么輔文的法條定位和存在意義也就蕩然無(wú)存,因?yàn)槿魏我环N情形都可以在主文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進(jìn)一步解釋?zhuān)橇⒎ㄓ趾伪卦谥魑闹蟾郊虞o文予以補(bǔ)充或者限制?這顯然違背基本的法理精神和立法目的。
當(dāng)然,按照《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xiàng)的規(guī)定,職工如若突發(fā)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shí)之內(nèi)經(jīng)搶救無(wú)效死亡的,可以視同工傷。然而,本案中,職工突發(fā)疾病并未出現(xiàn)死亡或者48小時(shí)之內(nèi)經(jīng)搶救無(wú)效死亡的情形,而是出現(xiàn)植物人的狀態(tài),這在情理上是否可以將其視為與上述兩種規(guī)定類(lèi)似的情形從而通過(guò)擴(kuò)大解釋或者目的解釋納入到視同工傷的范疇,需要立法部門(mén)進(jìn)行系統(tǒng)的研究和回答,但是在目前《工傷保險(xiǎn)條例》第十五條尚未明確將其納入視同工傷的前提下,在司法實(shí)踐的角度不能突破法律的限定性規(guī)定而僅僅經(jīng)由所謂擴(kuò)大解釋將其納入到視同工傷的范圍。
【注釋】 {1}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語(yǔ)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2年版,第1187頁(yè)。
{2}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上冊(cè)),第54頁(yè)。
{3}【法】亨利•萊維•布律爾:《法律社會(huì)學(xué)》,許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頁(yè)。轉(zhuǎn)引自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上冊(cè)),第54頁(yè)。
本文地址:http://www.wnpump.cn/guandian/7155.html
上一篇:最高院及地方法院關(guān)于社會(huì)保險(xiǎn)爭(zhēng)議處理意見(jiàn)
下一篇:因交通事故間接誘發(fā)疾病認(rèn)定工傷的標(biāo)準(zhǔ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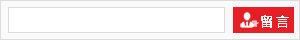









 冀公網(wǎng)安備13010202003181號(hào)
冀公網(wǎng)安備13010202003181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