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
工傷認定案件中,準(zhǔn)確界定“上下班途中”應(yīng)對目的和空間兩個要素予以考量,且采用目的解釋與文義解釋相結(jié)合的方法,以《工傷保險條例》傾向于保護職工權(quán)益的立法價值取向為基礎(chǔ),對“上下班途中”作出合理解釋,才能發(fā)揮《工傷保險條例》的保障功能,以維護職工合法權(quán)益。
【案情】
曹某某生前與原告濟南某機械制造廠存在勞動關(guān)系。2011年8月,曹某某由原告濟南某機械廠派遣至濱州地區(qū)無棣工地工作,是工地負責(zé)人之一。2011年8月11日,原告濟南某機械廠維修工劉某某到濱州地區(qū)無棣工地維修設(shè)備,當(dāng)日下午15時左右,劉某某維修完設(shè)備開車返回平明,曹某某同車返回。2011年8月11日20時15分,劉某某駕駛的車輛行至濟南市長清區(qū)孝里鎮(zhèn)路段時,發(fā)生交通事故,曹某某當(dāng)場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責(zé)任認定書認定曹某某無過錯。2012年,曹某某之子曾提出工傷認定申請,濟南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作出曹某某系工傷的認定書,本案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審理認為工傷認定書適用法律、法規(guī)錯誤,判決予以撤銷。2013年被告再次作出曹某某屬于工傷的認定書,原告不服,再次起訴。
【審判】
濟南市歷下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為:第一,《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第6項規(guī)定的“在上下班途中”系指以上下班為目的往返于單位和住處之間的途中。由于不同行業(yè)領(lǐng)域工作性質(zhì)具有多樣性,故這里的“單位”、“住處”均不能作簡單機械理解。“單位”既可以是職工所在單位的主要經(jīng)營場所,也可以是派駐外地的分支機構(gòu),或者是因工作需要臨時設(shè)立的工作場所等。這里的“住處”,既可以是單位安排的職工宿舍,也可以是職工家庭住址等。本案中,職工曹某某的家庭住址在平陰縣,雖然其被派往濱州地區(qū)無棣工地后一直在工地吃住,但這并不能絕對排除其從工地返回平陰縣的家中屬于下班途中。第二,職工曹某某是單位派駐無棣工地的負責(zé)人之一。事發(fā)當(dāng)日,曹某某搭乘劉某某的車離開無棣工地時工地停電,恰逢曹某某身體有疾需回平陰看病。曹某某未請假的行為即使違反了單位有關(guān)勞動紀律,但系另一法律關(guān)系,對工傷認定結(jié)論不產(chǎn)生實際影響。所以,被告濟南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作出的工傷認定書主要證據(jù)充分,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法規(guī)正確,原告濟南某機械廠的訴訟請求無法律和事實根據(jù),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56條第4項之規(guī)定,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評析】
本案當(dāng)事人對事實沒有爭議,分歧在于如何理解“上下班途中”。《人社部辦公廳關(guān)于工傷保險有關(guān)規(guī)定處理意見的函》中規(guī)定,“‘上下班途中’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時間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這一解釋雖然限縮了“上下班途中”的法條表述,但何為“合理”仍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標(biāo)準(zhǔn),導(dǎo)致實踐中認識不一,做法不一。筆者認為,要想正確理解“上下班途中”,應(yīng)采用目的解釋與文義解釋相結(jié)合的方法,以《工傷保險條例》傾向于保護職工權(quán)益的立法價值取向為基礎(chǔ),對“上下班途中”做合理解釋,才能發(fā)揮《工傷保險條例》的保障功能,以維護職工合法權(quán)益。
一、“上下班途中”的認知基礎(chǔ)
《工傷保險條例》立法價值傾向于保護職工權(quán)益,主要有四方面的理由:一是《工傷保險條例》第1條的規(guī)定把保障職工獲得醫(yī)療救治和經(jīng)濟補償放在了立法目的的首位,這也是《社會保險法》第1條規(guī)定的“使公民共享發(fā)展成果”的具體體現(xiàn)。二是《工傷保險條例》實行無過錯補償原則,只要因工致傷,除第16條規(guī)定的3種情形外,不論職工是否存在過錯,均可認定工傷。三是從《工傷保險條例》的修改過程看,認定工傷的范圍越來越大,第14條第6項適用范圍也越來越寬泛。四是從工傷管理部門的代位求償權(quán)條款看,《工傷保險條例》具有明顯社會保障功能,以確保受傷職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綜上所述,《工傷保險條例》傾向于保護職工權(quán)益,在這一認知前提下,應(yīng)從傾向保護受傷職工權(quán)益出發(fā)界定“上下班途中”的含義。“上下班途中”文意為上下班路上,可解釋為上下班和道路上兩部分,進一步解釋則是為了上下班而往返于居住地與單位間的道路上,這表明“上下班途中”有兩個基本要素,即為了工作的目的要素和道路上的空間要素。
二、“上下班途中”目的要素考量
因工的目的要素在理論上容易理解,但實踐中往往因個案的復(fù)雜性而被忽略。筆者認為,目的要素是前提,具有決定性,在判斷是否屬于“上下班途中”時,要首先考量目的要素,若不是為了工作而往返于居住地與單位間的道路上,則直接排除認定工傷。那么,目的重合時能否認定工傷呢?比如上班時一塊送孩子上學(xué)的,這是實踐中經(jīng)常遇到的問題,筆者認為能夠認定工傷。首先,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不斷發(fā)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生活節(jié)奏越來越快,單一目的行為現(xiàn)實工作生活中很少,要求純工作目往返于居住地與單位間的道路上失之過嚴,不符合經(jīng)濟和效率原則。其次,《工傷保險條例》傾向于保護職工權(quán)益的立法價值傾向,對目的要素作出可能的解釋符合立法本意。第三,目的重合不必然導(dǎo)致發(fā)生交通事故,也不必然增加交通事故的發(fā)生幾率。所以,單純就目的要素而言,在目的重合的情況下,應(yīng)該認定工傷。
三、“上下班途中”空間要素考量
途中是描述性概念,靜態(tài)而言是某段路線,動態(tài)而言是行進在某段路線上的過程,“上下班途中”中的“途中”應(yīng)為靜態(tài)的路線。線由若干點組成,最關(guān)鍵的點是起點和終點這兩點,起點和終點確定了,是不是“途中”也就確定了。上下班途中的起點和終點(起終點可以互換)是單位和居住地基本沒有爭議,但如何理解單位和居住地,兩者的范圍有多大,往往存在爭議。單位的范圍相對好確定,如上述案例所言,既可以是職工所在單位的主要經(jīng)營場所,也可以是派駐外地的分支機構(gòu),或者是因工作需要臨時設(shè)立的工作場所等。居住地相對復(fù)雜,應(yīng)包括經(jīng)常居住地、實際居住地和不定期居住地。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生活條件的改善,職工居住地可能有多處,職工本人可能有多套房屋,也可以為生活方便與父母子女共同居住,在工傷認定案件中,居住地應(yīng)以實際居住為判斷標(biāo)準(zhǔn),不能限定在住所地、職工宿舍或單位安排的臨時住處。
此外,關(guān)于合理上下班時間的問題,筆者認為,時間不是確定“上下班途中”的決定性要素,遲到、早退、晚走等只要符合上下班途中的目的要素和空間要素,均應(yīng)認定為上下班途中。
(作者:劉科,單位:濟南市歷下區(qū)人民法院)
本文地址:http://www.wnpump.cn/lunwen/6588.html
上一篇:加班費爭議處理指引
下一篇:勞動者起訴用人單位賠償社會保險損失的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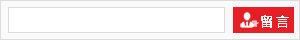









 冀公網(wǎng)安備13010202003181號
冀公網(wǎng)安備1301020200318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