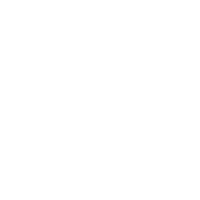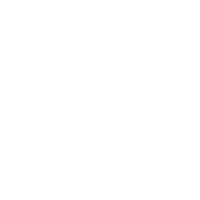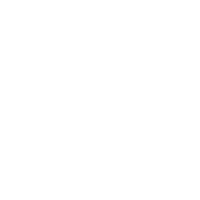媒體關注
吃手的機器:景縣斷指工人維權困境調查

路國榮無助地站在工廠門口。

幾位工人的斷手。燕趙都市報記者王小波/攝
■調查人:本報記者王小波
■調查地點:石家莊、衡水、山東德州
■調查事件:景縣河北德納V型輪有限公司頻頻發生斷指事故,據不完全統計,這家工廠已經有18名工人慘遭機器斷指。路國榮,遭遇斷指的惟一一個維權者,在向廠方維權時,先是申請一次性傷殘補助金被拒,而向勞動部門申請仲裁,卻被仲裁得需要倒貼錢。這家工廠為何不斷發生斷指事故?工人維權又因何走入困境?
1 “沒錢的怎么擰得過有錢的?”
從法院遞交完訴狀出來,路國榮就后悔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不停地問自己:“這樣做值嗎?可別為一時之氣得不償失啊?”奔波近兩年,結果比預想的還要糟,她有些疲憊。
昔日的工友們也善意地提醒她:“胳膊擰不過大腿,你沒錢,現在工作也沒有,老板有的是錢,你怎么和他擰啊?”
路國榮原來在景縣河北德納V型輪有限公司工作,從1990年起她就進了這家工廠,10多年中,她親眼目睹了一些工友的手指被工廠機器“吃掉”,但她怎么也沒有想到厄運有一天會降臨到自己頭上。2005年12月5日中午11時左右,旋軋車間的一臺機器突然沖下來,路國榮感到一陣鉆心的疼痛,她的左手食指已經血肉模糊。經過景縣人民醫院的處理,路國榮的左手食指只剩下半截。
同其他受傷工人一樣,路國榮想選擇息事寧人的方式來處理這次工傷,以便繼續留在這家工廠工作。2006年4月,路國榮以受傷為由找到廠里要求調換工作,她想去包裝車間,廠長王書生說“開會研究研究”,此后,路國榮多次找到廠里,得到的都是這句回答。
路國榮受傷后第二天,她的工資就被停發了,此后廠里再沒有給過她一分錢。意想不到的麻煩還在后頭。2006年9月,路國榮被鑒定為9級傷殘。勞動部門告訴她,可以一次性領取傷殘補助金4480元,但需要所在單位加蓋公章。路國榮拿著表格去工廠蓋章,去了10來趟愣是沒辦成,廠里一開始以章丟了、別人拿走了等各種理由搪塞她,后來干脆告訴她,“這事兒不該由你來辦”。
一次性傷殘補助金領不出來,路國榮向工廠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廠方告訴她,這屬于違約行為,她和工廠簽訂的5年期勞動合同還有4年多才到期,中途解約的話,她得賠工廠2萬多元。2萬多元?路國榮在這家工廠掙得不多,“少的時候每月才掙三四百元,多時也不過800余元。”無奈之下,路國榮托關系找廠長,表示還愿意在這家工廠工作,前提是工廠支付給她一點傷殘損失,“大家私了算了”。
她的要求遭到了廠長王書生的拒絕,王書生說:“建廠以來沒有這個先例,從來沒有給誰賠償過,工人也沒有要求,如果開了這個口子,下面都來要,我上哪兒弄錢去!”
雙方的商談不歡而散。“我和我公公一同去找他,王書生對我們說:‘勞動局、安監局,愛上哪兒告上哪兒告去,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我公公聽到這話后,氣得直打哆嗦,回去輸了幾天液。”路國榮說。
一截斷指惹來了這么多麻煩。本想自己給自己討點說法,說法沒討成,公公被這事兒氣病,因為心里窩火,路國榮夫妻倆打起了嘴仗,甚至鬧著要離婚。由于沒有經濟來源,路國榮想在縣城里找份別的活干。起初她去工廠里應聘,別人一看她的手就不言語了。后來,她去餐館應聘服務員,老板說:“媽呀,你這手,哪個客人見了還有食欲啊?!”
難道沒地方討說法了嗎?路國榮找過縣長,找過主管科局,都無濟于事,她想到了放棄。在深圳工作的哥哥告訴她,“這事兒要發生在我們這里,該是多大的事啊,你怎能說放棄就放棄呢?”2006年11月,抱著一線希望,她向景縣勞動局仲裁科申請勞動仲裁。
2 勞動仲裁讓她“得不償失”
就在路國榮向勞動部門申請勞動仲裁后不久,河北德納V型輪有限公司于今年1月27日向景縣勞動仲裁委員會提交了答辯書。
答辯書中說,路國榮要求解除勞動關系,屬單方面違約,應賠償該公司5000元/年×4年6個月計22500元,該公司還稱路國榮是從事技術工種的職工,合同期每少服務一年,應賠償企業5000元,這樣也有22500元。另外,路國榮不去該公司上班,違反了公司“關于加強勞動紀律的暫行規定”,“規定發生一天曠工扣當月3天平均工資”,計15048元。這樣,路國榮總計要賠償河北德納V型輪有限公司60048元。
工廠方面態度強硬,不同意調解。今年4月7日上午,景縣勞動仲裁委員會對此案進行了仲裁。
路國榮當時的代理律師許朝華覺得案子仲裁時有些滑稽。在開庭前,許朝華提出查看對方的證據,遭到勞動部門拒絕,“法律規定律師有庭前閱卷權”。更令人瞠目的是,廠方的委托代理人之一車國林,其身份竟然是河北德納V型輪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工會本來應該是工人權利的代言人,現在卻代表廠方與工人走到了對立面。”許朝華對此不能理解。
最后的仲裁結果令人大跌眼鏡:景縣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支持路國榮在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醫療補助金、一次性就業補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資、住院期間伙食補助費等5項請求,共計27450元。但廠方的部分請求也得到支持,路國榮得向廠方支付違約金19583.3元,以及她向廠方借款支付醫藥費的余額745.7元。仲裁處理費雙方各承擔1000元。
也就是說,最后廠方只需要向路國榮支付7112元,如果減去路國榮應得的4480元一次性傷殘補助金,減去她所支付的律師費和仲裁費,路國榮不但一分錢也沒有拿到,還要倒貼錢!
“且不說路國榮到底需不需要向廠方支付違約金,單就這起勞動仲裁來說,路國榮申請工傷待遇與廠方要求的違約賠償不是同一法律關系,怎么能放在同一個案子里來仲裁呢?”許朝華至今看不明白這份仲裁結果。
拿到這個結果,路國榮的心涼了。
但是仲裁結果已下,路國榮扳轉逆勢的惟一希望是向法院提起訴訟。她查閱了有關工傷賠償的法律網站,并通過網站聯系到了石家莊律師張士謙。張士謙告訴她,違約金不應該在這起案件中出現,另外,按照《工傷保險條例配套規定》,職工在工傷后有權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根本不存在違約一說。
律師的話又點亮了路國榮的希望。不過,景縣勞動仲裁委員會的這份仲裁結果打擊了很多有維權想法的工人。路國榮的筆記本上記著16名斷指工人的姓名和電話,他們都是在這家工廠工作時受傷,很多人受傷后沒有申請工傷鑒定。
當初路國榮申請勞動仲裁時,很多受傷工人都表示愿意出來作證,“去吧,我們支持你!”這些溫暖人心的話語伴隨著路國榮一路走到現在。看到這個結果后,很多人開始躲著路國榮,一些人干脆告訴她:“還是認了吧。個人怎么弄得過工廠?”還有工人給路國榮傳話說:“老板說了,寧肯把錢扔在法院,也不會給你。”
3 強勢工廠弱勢傷者
這家工廠的部分職工告訴記者,老板之所以如此強硬,還是因為害怕路國榮事件撕開一個口子后,受傷工人會接二連三地祭起維權大旗。
河北德納V型輪有限公司成立于上個世紀80年代,起初是一家縣辦企業,2004年改制為股份制企業,在改制前已擔任多年廠長的王書生出任改制后公司董事長。到工廠之前,王書生曾供職于景縣醫藥公司。這家工廠主要為客戶提供皮帶輪等零配件,在該廠門口懸掛著一塊顯著的標牌———“上海桑塔納轎車國產化共同體成員單位”。
這樣一張大旗并不能避免該廠接二連三地發生工傷事故。據不完全統計,這家工廠至少有18名工人被確認軋斷手指,而平時軋傷手指事件更是家常便飯。
1988年9月,工人張軍被軋斷了左手食指,成為該廠第一起斷指事故。不過,張軍說自己比路國榮幸運,“因為那時工廠還是國有企業,醫藥費廠里報銷,住院休養期間基本工資照拿,傷愈后又被安排到了檢驗科。”
打那以后,斷指和軋傷手指事故便時有發生,受傷工人的境遇也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
張軍的妻子華(化名)也在這家工廠工作,她的手受過5次傷,最重的一次右手食指被軋斷。華的斷指和手上的傷痕觸目驚心,在她最后一次“受大刑”后,她才得到“赦免”,去了包裝車間。一些朋友開玩笑說,張軍夫婦斷指也搞“夫唱婦隨”,還是“左右對稱”,沒有人知道斷指對他們生活造成的影響和這背后的辛酸。
實際上,路國榮也不是第一次受傷,到工廠的第二個年頭,她的手就被機器“啃”了一口,右手無名指和小手指變形。那次受傷后,她沒有提出任何要求,那時候這家工廠是縣城里的好企業,縣城里的人都帶著艷羨的眼神看著工人進出工廠,且那次受傷后路國榮工資照拿,外人從這里看到了“國有企業的優越性”。
阿飛(化名)現在是山東德州一家工廠車間的班組長,只有他伸出左手來才發現沒有無名指,他的指頭正是在河北德納V型輪廠工作時被機器“吃掉”了。阿飛出事之前,他的車間主任老楊也被機器“吃掉”一個手指頭。談及受傷的手,阿飛不無悔意,他受傷后連一次性工傷補償都沒有拿到。
“哪個工廠不出工傷事故?但像河北德納V型輪廠出這么多事故不正常,出一起事故應該舉一反三,加強安全生產教育,這個廠講得很不夠,所以前頭出事故,后頭又出了。出了事故后工人權益沒有保障,工人白受罪,勞動條件沒有改觀,對誰也沒有觸動。個人對工廠太難了。”阿飛說。
阿飛介紹說,當時在這家廠子里,常有離合器失靈的現象,離合器一失靈機器就突然沖下來,人再快也躲不過機器。時間一長,工人們都知道哪臺機器性能好,哪臺機器可能要“發威”,都找好用的機器。“照理說,工廠應該維護好機器,給工人提供安全標準的生產環境。”
7月11日下午,記者在這家工廠的旋軋車間看到,工人們正在把一個鐵片狀的東西放在操作臺上,大型的液壓機器往下一沖鐵片便被軋成凸凹狀。如果工人的手拿開不及時,或機器失控,工人的手指就危險了。一位工人說,20天前,一位名叫王瑞強(音)的工人剛被軋了手指。
對這些潛在的危險,工人們似乎習以為常,他們只是對報酬不高頗有怨言。工人們說,這家工廠實行計件工資,像這樣一道工序,一件成品可掙兩分錢,做1000件才掙20元,這還算收入不錯的一道工序,有的一道工序做一件成品才掙幾厘錢。
路國榮不服景縣勞動仲裁委員會的裁決,向景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后,河北德納V型輪有限公司在提交給法院的答辯狀中稱:路國榮在操作過程中,為圖干活快,多掙錢,私自調小機器的滑塊行程,屬個人違規操作造成。而該廠一位工人反駁說,個人調小機器的滑塊行程不大可能不說,如果一定的勞動強度能讓工人吃飽飯,工人何必自己加大勞動強度來掙要命錢呢,如果工人的待遇得不到提高,能不出事么?
律師則認為,即便是工人私自調整行程滑塊,出了工傷事故責任也在廠方,因為工廠與工人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工傷事故的處理適用無責任補償的原則,即責任無論是否屬于勞動者本人,受害人均應無條件得到一定經濟補償。況且事故責任的認定不能由廠家說了算。
路國榮向法院提起訴訟后,河北德納V型輪有限公司在提交給景縣人民法院的答辯狀中,措辭更為強硬,還要求路國榮賠償公司26萬余元。公司方說:“路國榮本人在公司工作期間,組織觀念淡薄,我行我素、不思進取、好逸勿(應為“惡”,記者注)勞。”路國榮的維權也被視為“肆意捏造事實、詆毀公司名譽,與公司離心離德”。公司還稱“對路的無理取鬧與無理要求我公司全體員工表示強烈不滿與抗議”。
盡管多年來多次發生斷指事故,這家工廠還是照常高枕無憂地生產。遭遇工傷后,工人們大都忍氣吞聲,絕大多數工人沒有申請工傷鑒定,沒有得到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很多人惟一的希望是繼續留在這家工廠工作,因為在縣城里找一份工作太難了。
“維權?想都不敢想。誰能餓著肚子和一家財大氣粗的工廠對著干?”一位斷指工人半開玩笑地對記者說。維權還是丟工作?工人們寧可相信老板在這座縣城里的“能量”。
4 通向維權的路有多漫長
在很多人看來,像路國榮這樣拿起法律武器和工廠對簿公堂,是一件概率極小的事件。這種小概率事件中的主人公大抵要具備幾個條件———一是要個性鮮明,二為工傷者是本地人,三是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迄今為止,路國榮在打官司的路上已花費了近8000元。
“這對一家工廠來說算不了什么,但對并不富裕的工人家庭來說是項大負擔。所以大家都認為我贏不了。”路國榮說。這種不對等讓工人在維權上天然地處于劣勢。
工廠工會主席在勞動仲裁時站到了工廠一邊,把勞動仲裁當作一根稻草的受傷工人并不滿意仲裁結果。對于這份勞動仲裁結果,負責此案的景縣勞動局仲裁員王興明說,這是在“尊重事實、尊重法律”基礎上得出的結果,至于路國榮提出的她的工傷待遇與廠方要求的違約賠償并不屬同一法律關系,王興明說,“這個案子是請示了衡水市勞動局仲裁科科長趙夏征(音)后得出的結論。”景縣勞動局不愿意就此事多談。
那么,這家工廠發生這么多斷指事故,當地的勞動監察部門在事前有無盡到勞動監察職責呢?
對這一問題,景縣勞動局辦公室張主任告訴記者,勞動監察人員都下去檢查了,對這家工廠的勞動監察情況,會給記者一個回復,但截至記者發稿時,沒有收到對方任何回復。這位辦公室主任說:“我覺得出現這樣的問題,主要問題不在勞動部門,負有主要監管職責的應該是安監局吧。”
接二連三發生工傷事故,河北德納V型輪有限公司安全生產條件是否達到標準?安監部門是否了解這一情況?景縣安監局辦公室主任句風亭說:“這事你應該去問企業。”
當地監管部門的推諉,代理或多起勞動維權案件的張士謙并不感到意外。重勞動仲裁輕勞動監察在一些地方已成為慣例,這也成為工傷事故頻發、勞動者維權成本高昂的重要原因。這種被稱為“訴前強制仲裁制度”已經在社會上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詬病。監管部門事前不作為,事后弱勢的當事人往往不服仲裁結果,工傷者要么放棄維權,要么進入繁瑣的訴訟程序,抬高了勞動者的維權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
張士謙認為,現行的維權機制對勞動者來說有很多不科學的地方,最突出的表現在于程序太復雜。如果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沒有簽訂勞動合同,走法律程序至少有11個,等到最后判決一般是3年之后,外地人根本耗不起。即使雙方簽訂了勞動合同,經過法院一審、二審最后也得一年半左右。
在張士謙過去代理的一些案件中,他還看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問題:用人單位不與職工簽用工合同,一旦發生工傷或欠薪,不能確定勞動關系便不能走勞動仲裁程序。有的單位對事實勞動關系沒有異議,一些基層勞動部門卻要“依法確定走法律程序”,讓工人陷入被動,如果確立不了勞動關系,工人連工傷都沒法認定。
相比這些維權無門者,路國榮還算“幸運”的,至少她和工廠有一紙勞動合同。對這起工人維權案,河北德納V型輪有限公司究竟有何考慮?記者聯系到王書生,王稱正在德州看病,第二天上午可以和記者見面。但等到第二天上午,王書生又推說在石家莊看病,王說:“這事已經走法律程序了,法院會給個說法。發生多起工傷事故并不是一次發生的,總不能都是我們的責任吧。”
“根據以往的案例來看,路國榮維權一案,路的勝訴基本沒有懸念,只是耗一個時間增加維權人成本的問題。”張士謙說。
媒體報道鏈接地址:http://news.sina.com.cn/c/2007-07-17/015013460330.shtml





 冀公網安備13010202003181號
冀公網安備13010202003181號